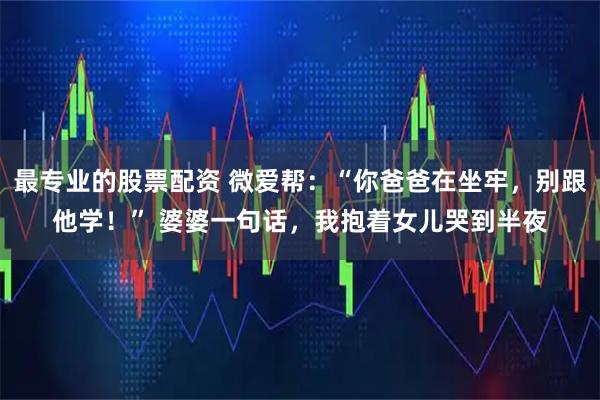
昨天晚上最专业的股票配资,我又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万箭穿心。
女儿妞妞才五岁,在幼儿园画了一幅画,兴高采烈地举着跑回家。画上是歪歪扭扭的三个人:扎小辫的她,长头发的我,还有一个,是她凭记忆和想象画的、戴着眼镜的爸爸。
她小脸红扑扑的,指着那个蓝色的小人说:“妈妈你看!爸爸从电话里走出来啦!”
我的心,当时就像被泡进了一缸温水里,又酸又软。我男人进去一年零三个月,妞妞都快忘了被他抱着是什么感觉了。这幅画,是她心里给爸爸留的那个位置,还在冒着热气。
可这口气还没喘匀,婆婆闻声从厨房出来,在围裙上擦了擦手,拿过那幅画。她盯着那个蓝色的“爸爸”,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,像是看到了什么脏东西。
下一秒,在我和妞妞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——
“刺啦——!”
那幅画,被她从中间狠狠撕成了两半。
“跟你说了多少遍!不要提他!不要画他!你爸爸在坐牢,他是坏人!你别跟他学!”
空气凝固了。妞妞的小嘴从惊讶的O形,慢慢撇下去,然后“哇”地一声,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。那哭声里,有被惊吓的恐惧,更有心爱之物被摧毁的绝望。
展开剩余74%我整个人像被钉在了地上,血往头上涌。我想尖叫,想冲上去把画的碎片抢回来,想对着婆婆吼:“你凭什么!你凭什么撕碎孩子心里最后一点念想!”
可我看到婆婆那双浑浊又带着某种偏执的眼睛,那里面没有恶意,只有一种她认为绝对正确的、近乎残酷的“保护欲”。我的话卡在喉咙里,变成了一团棉花,堵得我呼吸困难。
晚上,我把哭到打嗝的妞妞哄睡。她蜷缩在我怀里,睫毛上还挂着泪珠,睡梦中时不时抽泣一下。我看着她,眼泪终于决堤。
寂静的夜里,我只能把脸埋进枕头,死死咬住嘴唇,不让哭声太大。肩膀抖得像个筛子。
疼,真的太疼了。
疼的是婆婆那句话,像把刀子,不仅否定了我丈夫,更差点割断了我的孩子和父亲之间的血缘纽带。
疼的是我的无力。在这个家里,我像个孤军奋战的士兵。婆婆觉得她在“拨乱反正”,在教孩子“明辨是非”。可她不知道,她正在用最粗暴的方式,给妞妞的心里刻下一道可能一生都无法愈合的伤痕——“你的爸爸是坏人,所以你身上也流着坏人的血。”
这让我想起上次探视,他隔着玻璃,眼睛红得吓人,哑着嗓子对我说:“我最对不起的,就是妞妞。你告诉她,爸爸……爸爸很想她,爸爸在努力变好,早点回去抱她。”
一个在里面拼命忏悔,想“变好”的父亲。一个在外面,被至亲奶奶定义为十恶不赦的“坏人”。
我的孩子,到底该信谁的?
她未来的人生里,该如何面对“父亲”这个角色?是带着羞耻和憎恨,还是能理解世界的复杂,在废墟里,依然能辨认出那一丝叫做“爱”的东西?
这场战争,没有硝烟,却关乎我女儿的灵魂。
后来,我没再和婆婆正面冲突。我知道,那是两个时代、两种观念的碰撞,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我悄悄捡起了那些被撕碎的画片,用胶带在背面小心翼翼地粘好。
然后,我打开手机,点开了那个已经成为我精神支柱的红色图标——【微爱帮】。我让妞妞对着话筒,把她想对爸爸说的话,连同那幅画的委屈,都说了出来。我帮她拍下粘好的画,上传。
“爸爸,”妞妞带着鼻音,小声地说,“奶奶把我的画撕了,我哭了。但是妈妈又粘好了。爸爸,你不是坏人,对吗?我想你。”
几天后,他的回信来了。信很长,字迹有些潦草,能想象他写的多么急切和用力。
他给妞妞写道: “妞妞,爸爸做错了事,所以要在很远的地方上课、学习,就像你做错了题,老师会让你改正一样。爸爸非常、非常想你,每天都在想你。谢谢你为爸爸流的眼泪,这比任何惩罚都让爸爸难受。请你相信,爸爸正在努力做一个能让你骄傲的人。等着爸爸,好吗?”
我把这封信,读给了妞妞听,也“无意间”让婆婆听到了。
屋子里很安静。婆婆没说话,转身又回了厨房。但那天晚上,她破天荒地给妞妞蒸了一碗她最爱吃的鸡蛋羹。
我知道,坚冰不会一天融化。
但至少,我们开始搭建一座桥,一座用信件、用话语、用不肯放弃的爱搭建的桥。它跨越了高墙,也正在试图跨越人心的隔阂。
我不想我的女儿在仇恨和切割中长大。我想让她知道, 爱,是一种能力。它需要我们即使在最不堪的境地里,也有勇气去连接,去相信,去等待。
这座桥最专业的股票配资,我会一砖一瓦地搭下去。为了妞妞,也为了我们这个,还在等待完整起来的家。
发布于:河南省涌融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